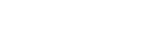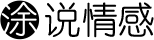好的感情,是可以滋养人一生的。哪怕只有几天、几小时、几分钟。
今天七夕,谁的爱情最动人呢?是年轻人轰轰烈烈的浪漫?还是父母爱情的细水长流?
记得在电影《我爱你!》采访明星的环节里,一个记者问几位老戏骨:
“电影全部讲的是老年人的感情生活,老年人真的还需要爱情吗?”
惠英红表现的很激动,她说:
“对不起,我们需要爱情。如果这打扰到你我很抱歉,但我真的很需要!”
01
人生第一次,“我爱你”
那一刻,这位金光闪闪的影后或许又想起了那段短暂而刻骨铭心的初恋。
那年惠英红13岁,从3岁开始,因为爸爸被骗光了钱,惠英红只能沿街乞讨,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十年。
十年间,惠英红受尽了白眼。
她说他们一排人坐在街边乞讨,有人路过就会看人,希望看到一个心地善良的施舍一碗粥钱。
运气好了,不用盯人看就会给钱;运气不好,就会被打。
说起这些往事惠英红云淡风轻,但很难想象,对一个几岁的小女孩来说,每天看人眼色时不时被打的日子是多么难挨。
几年后,惠英红没有办法,开始学着给美国大兵卖口香糖。

有一天,惠英红发现一个美国大兵一直在看她卖口香糖。
他们遥遥的打个招呼,大兵很自然的开始聊天,聊自己的身世,远渡重洋的漂泊。
惠英红也开始小心翼翼说起自己从没被人好好对待的生活。
末了,大兵为了让惠英红早点回家,买完了惠英红所有的口香糖。
第二天、第三天,大兵又来了。他和惠英红聊天,听惠英红讲她从没说过,也没人愿意好好听的话。
大兵默默的听着、看着,然后买完她所有没有卖光的口香糖,让她早点回家。

一直到第七天。大兵忽然问惠英红,粤语“我爱你”怎么说。
惠英红慢慢用粤语发出“我爱你”三个字的音。大兵就认真的学。
学完,一遍一遍对惠英红说:
“我爱你。”
那是惠英红如沼泽一般阴暗的人生里第一次有人对自己的说“我爱你。”
像一束光划破黑夜。
02
好的感情,可以滋养一生
小小的惠英红第一次知道,自己是可以被爱的。这个世界上还有人不会因为自己是乞丐,自己贫穷、卑微而嫌弃自己。
他说他爱我。
然后又听见,大兵说:
“我马上要去越南了,去打仗。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
说着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惠英红。他知道,多一块,惠英红就能少挨一顿饿,少受一个白眼。他在竭尽所能护她周全。
把钱都掏完,大兵看了一眼惠英红就走了。
没有回头。
这一走,就是一辈子。

几十年后,那个沿街乞讨的小女孩成了大明星。
连续两次拿影后,哪怕演个小角色,都能成为“TVB的金牌绿叶“,赶上了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香港武打戏里的扛把子“打女”;也是将近20年后文艺片里的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中间被冷落过、茫然过,但好在她都挺过来了。
她说:
“拿到每一个角色,我都会在心里想,我能不能做得再好一点?其实很多人会说你都到了这个年纪,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命?我的想法跟一般人不一样,人总会有离开的那天,我希望我离开的时候可以留下一些东西,一直流传。”
看遍人世繁华与落寞的惠英红大概经常想起五十年前的大兵和那个平淡却闪光的下午。大概就是那样一个下午,给了小小的惠英红人生之初的善良和光明,还有活下去的生命力。

好的感情,是可以滋养人一生的。哪怕只有几天、几小时、几分钟。
所以功成名就的惠英红不厌其烦的对媒体讲起那段往事,讲起自己曾经乞讨的经历,只是想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故事,多一个人知道,和美国大兵的重逢就多一丝微妙的希望。年过六旬的惠英红当然知道,在茫茫人海找一个50年前的故人有多难。但她还是保留最后一丝希望。她跑到美国办老兵慈善会,冒失的问在场的老兵:
“你们有人50年前去过湾仔吗?”
没有人说去过。
惠英红又问:
“如果你们有人认识去过湾仔的大兵,能不能帮忙问下他有没有见过一个绑着两根辫子的小女孩,记得让她找我。”
03
爱是权利,无关年龄
原来现实里,爱一人等一生的感情是真的存在。这比薛平贵和王宝钏的故事更绵长,也比梁祝的爱情更喜忧参半。
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里说,爱情是一场整个人类的瘟疫。躲不开、绕不过。
我想一个再麻木、再普通的人,在一生冗长的日子里,也有被爱情击中的时刻。不分性别和年龄。
我知道,在碎片化和及时享乐的时代,有话语权的人才能更充分的表达自己。不会用智能手机、不懂得怎么讨人欢心的人会被逐渐淹没在互联网里。
所以我们很难听见老年人的声音。他们的感情、他们的快乐、他们的遗憾都被忽略了。我们只记得他们是我们的奶奶、阿姨、姥爷、叔叔。
好像他们生来就是为了成为奶奶、爷爷、叔叔、阿姨。

和年轻人相关的可以是梦幻的爱情、热烈的友谊,而和老人相关的只能是早八的鸡蛋、小区里的广场舞,以及中午、晚上和明早的饭。
这是不公平的。
我们常说尊老爱幼,又常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但真正做到的人又有多少呢?
我们只是觉得让老人能吃饱喝足就算尽孝了,却不肯多花点时间听听他们的想法,听听他们的烦恼,听听他们年轻时的遗憾和快乐。
他们一直那样爱我们,我们却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不希望等到我七八十岁,也成为那个在小区门口拄着拐杖孤孤单单的老人。

我希望那时候我依然有我要好的姐妹、我想做的事、我能爱的人。不管我的爱绝望或平淡。
我只觉得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没有应该或不应该,是生而为人就会有的权利和需求,不会因为脸上多了几道皱纹就褪去或被剥夺。
我希望我老了以后,不会再有年轻人冒失的问我:
“你都这么老了,还需要有人爱吗?还需要爱情吗?”
如果有,我会对他说:
“如果你有,我也有。只是你太年轻,我不觉得你懂什么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