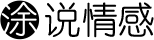多少女人的价值排序,把家庭放在第一位。她们的一生,都在为别人而活,为儿女,为老人,为伴侣,却唯独,不曾为自己活过。累,不是最难受的,最难受的是,至死都留有遗憾。
这两天,看到一个视频。
里面的故事,让人很是感慨。
65岁阿姨,在离婚后的8年骑行世界。
有人不理解,说她是乞丐,瞎折腾。
在被骂丢人时,她淡然回应:我喜欢现在的生活。
01
看世界,更是看自己
视频中,她戴着卡其色帽子,裹着深色围巾,眼睛小而有神。在镜头前,她用简单朴实的话语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她是河南郑州的李冬菊,她说:“我喜欢这样的生活,很多(经历)让我改变了人生,那是用金钱换不来的。”

谁也看不出,这个健谈、平和的女人,曾经因为离婚,得过严重的抑郁症,甚至一度住进精神病院。
8年的时间里,她一个人骑行泰国、法国、新西兰等12个国家,横跨三大洲。
不少人留言,表达了敬佩,但其实以前的她,从来没试过冒险。
年轻的时候,她在纺织系统工作,也在企业做过保管员,一天8小时都在机器边转来转去,很少与人打交道。
平日里,生活极其单调枯燥,两点一线,不是单位,就是家里。
夫妻俩相守到晚年,本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平静下去。
但突然有一天,丈夫对她说,他要离婚。
这之前,似乎没有一点预兆,对于那时的李冬菊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
她不理解,自己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
为此,她得了严重的抑郁症,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心烦,眼神发直,还住进了医院。
旅游,其实是她自救的方式之一。
但它真的起了作用,看世界的过程中,她慢慢就断药了。之后,她甚至忘了自己有抑郁症。

她是怎么旅游的呢?
别人出国旅游都要上万,她去泰国44天,却才花了2000元。
游历世界的过程中,她吃得很省,跟着当地老太太去超市,买打折食品。住得更省,只需搭帐篷,甚至还住过墓地。
就像她说的:“我不去和任何人攀比。”
她慢慢骑行,见过形形色色的生活,体验风土人情,感受人间温暖。
有一次,天气很热,高达40多度,她刚停下山地车,就有一位开越野车的女人过来,微笑着问她去哪。
接着,那个女人要送她一程,把她的山地车搬上越野车,热情地给她递水果和饮料。

到了地方后,女人也没让她下车,只说那里不安全,又继续开了六七十公里,等到了一个镇上,才放她下来。
结果她刚下车,又有两个人非要载她,想要送她一程。
知道她一个人骑行,很多人主动帮助她,还有人给她送帐篷。
所有这些,都让她很感动。
旅途的过程中,她整个人变化很大,越来越自信的同时,也越来越清楚,什么是她想要的。
一场看世界的骑行之旅,更是一场寻找自我的心灵之旅。有时候,只有勇敢推倒心中的那面墙,才能于山穷水尽处,见到美好春光。
世界上有太多人,都不敢走出舒适区。其实踏出的第一步最难,走出来就是勃勃生机。
02
人过半生,活一回自由
李冬菊的故事,不禁让人联想起,两三年前“抛夫弃女”自驾游的苏敏。
2020年的秋天,56岁的苏敏开着一辆车,从郑州出发,开始了一个人的旅程。
她是一位小个子女士,和和气气,一张圆脸,笑起来还能见着门牙缝。
她的目的,不是去哪,而是离开,离开让她喘不过气的生活,离开那段底色灰暗、苟延残喘的30年婚姻。
她过得并不幸福,夫妻俩也合不来,只是搭伙过日子。丈夫会经常挑刺、打压,两人几乎不交流,甚至很早以前,就分床而睡。
对于自己的家庭,她履行了社会意义上所有的母职,抚养女儿成人,帮忙看顾两个外孙,直到他们能够上学。
旅游的契机,来自于偶然看到的一段视频,是别人自驾游的场景。那段视频就像一道光,突然击中了她,那时她才知道,原来女人还可以这样活。

在做了齐全的准备后,2020年9月24日,她“出逃”了。
一人一车一路向南:三门峡、西安、成都、重庆、蜀南、昆明、大理、香格里拉……
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自由,没有害怕,没有孤独,只有自由。
她,也曾确诊抑郁症,每天服用希泰乐与解忧丸。在家的时候,经常性失眠,但神奇的是,自驾游的一路上,她却休息得很好。
因为感觉没那么需要,到了云南,她就把药停了。
不少人一直关注着她分享的旅游视频,他们有种感受,她比刚出发的时候年轻了,笑容也多了。

在直播中,她鼓励女人们大胆做自己。
她说:“我就是做了我自己想做的事儿而已,给咱们同龄的姐妹们,活成了他们想要的样子。”
苏敏,是多少中国式老母亲心向往之的样子。
年轻的时候,既要带孩子、做家务,又要忙工作、顾老人,好不容易熬到退休,仍然歇不了,还得为儿女带娃,买菜烧饭。
活到老、做到老,没有工资,也没有休息日,却被视为平常。
有人在她的账号底下留言说:
希望我妈妈也能这样,摆脱家庭牢笼,不要那么无私,事事为别人考虑,希望妈妈能自私一点,希望妈妈一直健健康康特别幸福。
之所以选择出逃的方式,是因为冗长的岁月里,无条件为家庭倾斜,没有为自己留一点空间。
03
每个人的归宿,都是自己
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有这样一句话:“我心目中的女性主义,是追求自由的思想,只要自由自在地活着,怎么样都可以。”
60岁那年,为家庭操劳了大半辈子的杨本芬,开始做一件从未干过的事,那就是写小说。
杨本芬是一位家庭主妇,她当过农民,切过草药,但跟写作不曾有过任何交集。
在四平米的厨房里,伴着油烟机的嗡嗡声,和灶上小火炖肉的咕噜声,她坐在一只小矮凳上,就着一条方凳,开始写作。
那时,她才当上外婆,在二女儿家帮忙照看外孙女,要做饭、哄孩子、收拾家,只能在忙里偷闲的缝隙里写东西。

杨本芬想写的,就是自己的母亲,一个经历过战乱、饥荒,承受过丧子、丧夫之痛的女人,在动荡的年代,拼了全力,养大了自己的孩子。
之所以开始写作,是因为那一年母亲去世,她陷入了无比的悲伤之中,她不想让母亲就这么消失,不愿意让母亲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就这么抹去。
作家野夫写了《江上的母亲》,来纪念亡母,写得催人泪下。他把伤痛在心里消化了10年,才敢提笔。
可杨本芬已经60岁了,她还有多少个10年呢?
岁月不等凡人,于是写作立马被提上日程。
几个月后,她就完成了11万字的《秋园》手稿,连她自己都难以置信。
后来的20年,她就这样不求回报地写着。
写到最后,所有手稿的分量,竟然重达8斤。
20年后,她的文字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秋园》,受到了读者的认可,豆瓣评分8.9,还入围了第一届PAGEONE文学奖。

多少女人的价值排序,把家庭放在第一位。
她们的一生,都在为别人而活,为儿女,为老人,为伴侣,却唯独,不曾为自己活过。
累,不是最难受的,最难受的是,至死都留有遗憾。
家庭,没有为她们做过什么,反而成了捆住她们的枷锁。她们没有成为理想的自己,甚至没时间照顾自己的感受。
人生最可悲的,不是多么劳碌,而是从来不曾乐过,一辈子逆来顺受、稳稳当当,却只是白活一场。
亦舒说:“每个人最终的归宿,都是自己。”
无论多少岁,都有活出自我的权利。

不是为了给谁看,也不是为了迎合谁,而是按着自己的喜爱,痛痛快快地活,热气腾腾地活。
向着无尽阳光,迎着四季和风,走自己的路,唱自己的歌。
还记得摩西奶奶吗?
她从小生活在农村,到了70岁才开始画画,却留下了1000多幅油画作品。
她的画作在MoMA展览,被大都会博物馆和白宫收藏,个人展览从美国展到巴黎、伦敦。
其实,不管什么时间,总有人觉得晚了,但摩西奶奶告诉我们,人生永远不算晚。
就像丹比萨·莫约说的,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